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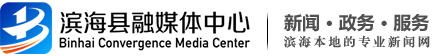
臧亚平
我的家乡滨海县拥有六百多公里航道,如脉脉清波,织成一片温柔水网。而我的老家五汛镇双龙村,更是被流水深情环抱——北倚苏北灌溉总渠,南临射阳河,西靠民便河,东接射北干渠。至于那些蛛网般密布的小河沟汊,更是数不胜数。在这片水乡,鱼虾自在游弋,为人们提供了最鲜美的食材,也成为我记忆里最鲜美的滋味。
初识戽鱼,约莫是七八岁的光景。母亲当时在村小任教,为响应“勤工俭学”号召,带着班上的大男生们,在我家老屋南边的鲈鱼港组织了一次戽鱼。那天一大早,母亲便领着班上朱德才、臧步开等十几个大男生来到河边。鲈鱼港东西蜿蜒二三里,宽不过七八米,水深约八九十公分。他们选择百来米的一段,开始了与河水的对话。
戽鱼先要打坝。学生们挥动铁锹,从河岸取来大块泥土,在水中筑起一道道堤坝。坝成后,他们取出从家带来的瓷盆,一盆接一盆地戽水。待水位渐低,河底的鱼开始慌乱跳跃,便插上用芦苇杆编成的“小薄子”,拦住想溜走的鱼儿。水将见底时,大大小小的鱼挤在“小薄子”前,学生们不慌不忙地往篮子里拾,太小的放回水中。鱼的种类很多,鲈鱼、鲫鱼、黑鱼、白条、鳗鱼、红眼丁子鱼等。
一段戽完后戽第二段,在坎上开个口子放水,余水再用瓷盆戽出,如此往复。那日收获百十斤鱼,我和弟弟在旁边也捡了七八斤,如获至宝。
我家房前屋后,铺展着无垠的农田。秋天稻子收割完毕,翻耕过的褐色土地,纵横交错着无数条三四十公分深的墒沟。这些不起眼的沟洼,便成了我们姐弟三人天然的“戽渔场”。
无需繁复的工具,一切信手拈来:姐姐眼疾手快,抱起轻薄的“小薄子”;我端着家里的搪瓷盆;弟弟扛着小铁锨,兴冲冲地跟在后面。选一段水稍深的沟子,七手八脚垒起泥坝,便开始我们的“大业”。三颗小脑袋挤在一处,合力舀水,看浑浊的水面一寸寸下降,心也跟着悬起来。
最令人屏息凝神的时刻到了!水将干未干之际,原本藏匿在淤泥里的小鱼小虾都惊慌失措起来,噼里啪啦地甩尾蹦跳,泥浆四溅。我们总是尖叫着争相扑进泥里去抓,小手在泥水里一通乱摸,溅得满身满脸都是泥点子。
然而,这份满载而归的喜悦,有时也会让母亲犯难。有几次,我们仨拎着沾满泥巴、活蹦乱跳的“战利品”兴高采烈地跑回家,灶台却正巧没了油。母亲看着水桶里亟待下锅的鲜鱼,又看看我们泥猴似的模样和期待的眼神,总是显得无奈。她叹口气,大声说道:“以后不准再去戽鱼了。”可田野的诱惑和捕鱼的快乐,哪是大吼几句就能拦住的?我们嘴上应着,转头又溜到了田边。
随着年龄增长,每到夏秋季节的周末,我常约同学去找地方戽鱼。我们选的多是几米宽的小水沟,一段段打坝戽水,常常从清晨忙到日暮。傍晚时分,我们常会齐声高喊:“戽啊!戽啊!加把劲啊!”有时热得受不了,见四下无女性,干脆脱个精光继续干活。即便浑身泥水,蚊虫叮咬,但看着活蹦乱跳的鱼儿,这些苦楚都不足挂齿,一个个都成了“泥人”仍奋战不休。最讨厌河豚,一碰就鼓成球,我们从不理睬;最怕昂刺,被它多次刺破手指;鳗鱼滑溜,有时得用鱼叉才能制服。
记得有一回放学,我与臧步伟四叔偶然瞥见一个三四十平米的水塘中有鱼影游动。两人心头一喜,赶忙回家取来戽水的家伙什儿。谁想这塘子看着不大,却有一米多深,我俩你一盆我一盆地戽了两个多钟头,才终于见了底。
这一戽竟收获了惊喜——足足五六十斤小鲫鱼,银亮的鱼身个个都有指头长,沉甸甸地装了两小筐。一时吃不完的,母亲便用细绳穿起,挂在檐下晒成鱼干。待到冬日,取些出来浸了黑酱,往饭锅里一蒸。那咸鲜的香气随着蒸汽弥散开来,就着这般滋味,空口也能扒下一大碗饭。
那时的农村,每逢戽鱼季节,到处可见忙碌的身影。有时大人戽过的地方还有漏网之鱼,我们小孩就会接着戽,直到水干鱼尽。我家北边百来米住着三奶奶一家,她家几个儿子都是戽鱼好手,村里人都戏称他们是“鱼蛆”。虽然劳力充足,但他家粮食总是不够吃——红烧鱼太下饭了。
如今,随着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,河里的鱼越来越少,戽鱼的热闹场景也再难见到了。那些与鱼共舞的欢乐时光,那些浑身泥水的酣畅淋漓,都成了记忆中最鲜活的画面,永远定格在那个水清鱼肥的年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