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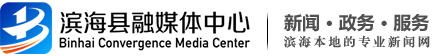
沈华山
初到姑苏城,我像被骤然拔离土壤的植株,连呼吸都带着陌生的滞涩。我来自苏北农村,黄海之滨的乡音带着海的开阔和淮河的酣畅,与眼下的吴侬软语截然不同。菜市场摊主的吆喝裹着小桥流水般的尾音,公交司机报站声黏软得像揉皱的糖纸,邻里笑容里藏着读不懂的语调褶皱。那些缠绕街巷的方言如细密藤蔓,轻轻隔开我与周遭,让我始终带着局外人的拘谨。
真正卸下我防备的,是租住小区楼下的梧桐树。某个黄昏散步时,阳光穿过掌状叶片织就的细碎金网,风一吹,光斑便在叶片间跳跃、流淌。这场景猝不及防地打开记忆:苏北老家院墙外的梧桐亦是如此,初夏缀满淡紫花穗,海风卷着花瓣粘在我童年的发梢,清苦里混着海腥。抚着树干,粗糙纹路竟与海风磨蚀的老家梧桐毫无二致。那一刻,方言的隔阂轰然消解,这株他乡梧桐以最沉默的方式,给了我最妥帖的安抚。
从此我格外留意身边的植物。晨跑时瞥见绿篱里的狗尾草,正是老家田埂、黄海堤岸石缝里都能扎根的模样,毛茸茸的穗子挺立着,和儿时追捉时沾着海沙的模样重合;办公楼花坛的太阳花顶着烈日盛放,单层薄瓣艳得晃眼,与母亲窗台那盆连傍晚收拢的弧度都分毫不差;便利店盆栽里挤着的马齿苋花,肥厚青叶绿得熟悉,让我想起奶奶挎着柳篮在田埂挖取的身影,她说这“长寿菜”带晨露潮气清炒最香。
这些植物像散落在他乡的旧信物,提醒我世界从未因地域而真正割裂。它们不问方言、不分地域,只循节律生长开花。老家时寻常的景致,在他乡成了最坚实的依靠。我忽然懂了,植物最擅坚守本质:无论江南烟雨还是北方风沙,梧桐照展掌叶,太阳花仍追阳光,狗尾草照结穗子。这份品性刻在基因里,从不受地域变迁影响。
更有意思的是那些面孔。小区晨练老人弯腰拉伸的姿态,像极老家村口晒暖的爷爷;菜市场阿姨捏着青菜翻拣的神情,与娘亲买菜时如出一辙;便利店收银姑娘找零时的笑靥,竟有高中同桌的影子。起初总忍不住想搭话,可陌生的方言会瞬间打碎熟悉感。后来渐渐释然:只要不开口,这些相似的神态动作,便都是认取“老乡”的暗号。
原来,植物春生夏长的节律不因地域紊乱,人善良勤劳的品性也不会被语言阻隔。就像老家植物到他乡蓬勃生长,他乡人来我老家亦会带着真诚——地域差异不过是表象,本质的相通才是联结的根基。
我们总执着于方言隔阂、地域差异,却忽略了共通的本质。植物用沉默告诉我,真正的联结从不是语言一致,而是本质相通。梧桐守着掌叶,人守着善意,社会运转亦如此——千差万别表象下,藏着对美好、生命与温暖的共同渴求。
如今,无论走向何方,我再不因方言而局促。摇曳的植物、熟悉的面孔,无不在诉说:美好天生就跨越地域。正如阳光普照万物,自然滋养众生,人心的温暖亦能轻易冲破语言的藩篱。这份来自自然的启示,让我在人生旅途上,始终怀揣着一份对世界的敬畏与善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