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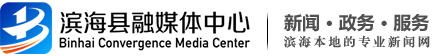
臧亚平
分田到户前,生产队每年秋收的景象,至今仍清晰地烙在我记忆深处。尤其是那割稻与打场的热烈场面,只要闭上眼,那片金黄、那些喧响,便立刻在心底苏醒。
我们生产队有两个用了多年的谷场,一个在东头臧正云家老屋旁,另一个在我家东北边臧步良家南侧。两个场子四周簇拥着低矮的小树、无边的农田和静静流淌的小河。割稻前一个月,队里就忙着“造场”。老水牛拉着沉重的石磙,一圈又一圈碾压着原本松散的场地,直到压得又硬又平。有时为了压得更实,石磙后还拖着一捆沾满泥浆的芦苇——那扎实的劲儿,仿佛要把整个秋天的分量都压进这片土地。
我记得,收割那几天,天还未亮透,各家的舌簧喇叭和生产队里那几个高音喇叭就响了起来。队长的通知回荡在晨雾中:“各家各户注意了,今天开始割稻!所有男女劳力带上镰刀,七点前到东大场西边稻田集合!”通知一停,家家户户匆忙扒几口早饭,便纷纷推门而出,向田里赶去。
那时准备收割的稻田多半还是水田,割稻人常常要站在漫过腿肚的水中弯腰作业,不像如今多是干田,收割机轰隆一过便是几亩。几十个男女劳力手持镰刀,在田里一字排开,一路向前割去。割稻是实打实的重活:左手拢住稻秆,右手挥镰贴地割下,再顺手把稻子整齐地铺在身后。动作看似简单,却要成千上万次重复,一天下来,腰都直不起来,实在累人。
割稻人的身后,多是跟着几个专门捆稻的男劳力。他们信手拈两把稻穗一拧就成了草绳,再利落地把稻子一捆一捆扎紧。
不多时,五六个男劳力赶着两条老水牛拉的小木船进了田。牛缓缓向前,他们就在船尾码放稻捆。船一装满,老牛便喘着粗气、吃力地拉动船只,向大场踱去。若是田里水太浅、船进不去,就只得靠男人们用扁担一担一担挑往大场。
稻捆一卸下,很快被整齐码放在场边。不出半日,二三十亩水稻便割完了,稻捆堆得像一座座金色的小山。这样的景象,在一块又一块田里不断重复上演。
当晚,全队劳力还要一起“放场”。大家把稻捆一个个拎到场地中央,解开草绳,将稻穗均匀地铺满整片场地。不到一个钟头,整个大场就变成一片金色的海洋。
接着是“碾场”,我们也叫“打场”。那时队里已有了手扶拖拉机。打场时,拖拉机拖着两个二三百斤重的石磙,冒着黑烟,在铺满稻穗的场子上不停地转圈碾压,直到所有稻粒全部脱落下来。开拖拉机的一般三四人轮班——现在回想,仿佛那时候每个大人都会开这铁家伙。碾完一场稻,常常得花五六个钟头。若稻子不多,也有人赶着老水牛,拉一个石磙,慢慢地、一圈一圈地碾。
第二天清早,一部分人继续下田收割,另一部分人则来到大场“翻场”。他们用铁叉挑起稻秆反复抖擞,让未脱尽的稻粒落下,再把秸秆叉到旁边晾晒。同时清理混在稻粒中的碎草,好让稻粒充分沐浴阳光。
要想把稻粒和稻草彻底晒干,每隔一两个钟头就得“翻第二遍”:用木制的探耙翻动稻粒,用铁叉翻晒稻草。
晒干之后,就开始“拢场”。大家用铁叉把稻草叉起往高处堆。堆到一定高度,就有两三人爬上去,将下面递来的稻草一层层码齐——这些稻草是冬日牲口的主要粮食。稻粒则被用“小刮板”、木锨和竹扫帚拢成一堆又一堆。
紧接着是“扬场”。男劳力们趁着有风,用木锨将稻粒高高扬向空中,风把草屑杂尘带走,留下饱满干净的稻粒。这活一个人也能干,但两人配合效率更高。我记得臧步喜、臧步军、杨正清、杨正有几人就常搭伙扬场。他们都戴着草帽,不然必定满头满身都是灰土。一人扬粒,另一人就拿着扫帚轻扫落在下风口的草屑。扫草的人仿佛站在一场“稻粒雨”中,稻粒噼里啪啦打在草帽上——那声音,在庄稼人听来,大概是这世上最动听的音乐。
扬干净的稻子被堆成小堆或长条的“山芋行”,上面用白石灰做标记,再蒙一层塑料薄膜——印记若被破坏,就知道被人动过。在稻子运进生产队仓库前,夜里还得派男劳力睡在场上看守。
分田到户后,我家分到了三亩七分二地,每年种一季稻、一季麦。收割的流程与从前大致相同。
如今回想,集体生产时期那套全靠人力的收稻流程,真是环环相扣、声声入心:造场、割稻、运稻、碾场、晾稻、晾草、翻场、拢场、扬场、看场……每一幕都如此鲜活、如此深刻。即便后来包产到户,每到收稻收麦,全家老小仍要把这套流程重新走一遍。那些汗水、那些协作、那些疲惫与欣慰,永远刻进了岁月的记忆中。
这些农忙时节的劳作虽辛苦,却收获了大地质朴而美好的馈赠。当金黄的稻谷终于归仓,当一年的期盼落地成实,农人们的脸上总会浮现出踏实而欣慰的笑容。那些被汗水浇灌的丰收,那些集体协作的温度,至今仍在记忆中熠熠生辉。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,机械化的农耕逐渐取代传统人力,但这些记忆永远不会褪色——它们是一个时代的印记,更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、珍贵的生命财富。